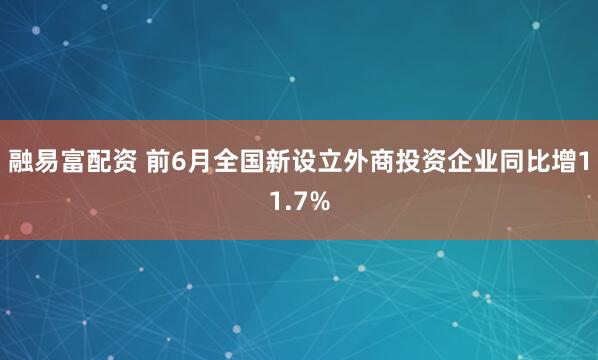2050年前后启远网,农村老年人口中40%以上将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迁移引起的结构性老龄化与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带来的自然老龄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未来,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加深,其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展
文 | 杜鹏
基于七普数据进行的人口预测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高龄人口规模将快速扩大。不同于当前超1.2亿农村老年人口中,低龄老年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年龄结构,2050年前后,农村老年人口中40%以上将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
准确把握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合理看待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社会的多重影响,是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应在明晰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基础上,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耦合,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中的地方创新潜能,将广袤乡村建设得更好更有活力。
养老服务供需结构性失衡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人口老龄化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生产与治理等不同领域具有全局性影响,合理看待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养老、乡村治理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多重影响,对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老龄化,最直接影响的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集中反映为养老需求增加与服务资源有限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迁移引起的结构性老龄化与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带来的自然老龄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导致农村养老需求快速增加。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乡村表现更为突出。
其一启远网,农村养老的制度化资源供给相对有限,难以应对当下农村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问题在农村集中显现。
其二,结构性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结果是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下降,快速的现代化、城镇化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完整性,家庭养老资源缩减,“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受到冲击。
其三,农村老年人掌握的养老资源不足,自我保障能力较弱。这不仅体现在农村老年人普遍享有的养老金水平较低,还体现在其参与生产、就业的途径主要集中在农业,而单纯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尚不足以完全保障老年人的全部养老服务需求。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深刻改变了农村社会的治理,重塑了基层治理的主体与内容等。
其一,年轻的高素质人口大量外流使农村人口结构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治理主体因此发生改变。在农村基层,部分干部受教育水平较低、年龄偏高,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不足,影响农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和效率。同时,在村居民年龄渐长,参与基层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日渐减弱。
其二,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的日渐老龄化,深刻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老年群体的需求成为治理的重要关切。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对农村养老与医疗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治理和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在向为老服务转变。
重视农业劳动力代际更替
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产生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的大规模城乡流动实质是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这一以较高受教育水平、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的择优性转移深刻改变了农业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老龄化成为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健康、体能等生理层面看,与青壮年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劣势明显。随着劳动者年龄增大,其可以承受的连续劳动时间减少、劳动强度下降,劳动生产能力降低。
从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信息吸纳能力等非体力层面看,老年劳动力对新技术的学习和认知能力有限,且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进而影响农业产出。
我国在劳动力质量流失条件下能实现农业的较快增长,说明劳动力老龄化及背后隐含的质量下降的负面影响尚在可控范围内。
其一,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长期存在启远网,农业部门不仅存在数量意义上过剩的劳动力,还存在质量意义上过剩的劳动力。所以,当前劳动力的择优性转移释放出附着在农业生产上的冗余人力资源,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由此提高。
其二,劳动力的择优转移意味着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代表更高的职业技能水平与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激励了农村家庭对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以,当前劳动力老龄化是基于与二三产业的横向比较,但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可能在社会人力资本增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因此尚未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明显制约因素。
其三,农业技术的进步、生产性社会服务的发展缓解了农业生产的年龄约束,增强了“老人农业”的生存能力,当前阶段并未对农业产出产生实质性影响。
同时,产生这一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老龄化程度仍较轻,农村老年人口多以低龄老年人为主。未来,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加深,其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将进一步发展。
提高应对老龄化的综合能力
我国即将进入的“十五五”时期,应在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方面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
“承前”指的是,持续推进“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这一任务。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首先应在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有所作为,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养老需求。应通过全面整合农村闲置资源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大量下乡资源,推动有需要的农村地区开展适老化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农村基本围绕养老展开,从“完善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服务工作”到“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老年人的角色被简化为被照料者。
面向“十五五”时期以及更长远的未来,政策应突破农村人口老龄化应对中的“养老”视角,更好把握乡村振兴提供的新机遇,夯实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基础,充分提高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启后”的发力点之一。
其一,以产业振兴兴旺乡村产业,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村家庭更好共享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通过增加区域人口的就业机会、利用农业现代化要素构建适老型农业、延展农村地区产业链等方式,增加老年人个体、农村家庭与村集体的收入水平,促进劳动力人口就近就业创业,夯实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与劳动力基础。
其二,以人才振兴全面提高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素质与人才储备。我国乡村振兴要求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明晰农村人口动态、掌握养老服务技能与管理知识等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以组织振兴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一方面,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健全优化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组织实施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切实把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转化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作为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老年群众组织,城乡社区基层老年协会是基层老龄工作的重要组织载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老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加强老年协会建设,搭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平台,健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组织体系。
其四,以生态振兴促进乡村适老化改造,打造宜居适老的乡村环境。通过垃圾治理、污水治理等为老年人提供绿色、环保、干净的居住环境;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同步推进乡村适老化改造。
其五,通过文化振兴建设乡风文明、老龄友好的农村社会。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孝亲敬老良好家风,重视发挥社区教育的作用,在村落中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良好风气,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活动,将农村建设成人人共享的老龄友好社会。

植保无人机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再生稻无人农场作业(2024年6月6日摄)陈振海摄 / 本刊
让广袤乡村更好更有活力
“启后”的另一个重点是,着重发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地方创新潜力,找准不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基础及与现实发展间的差距,通过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合理发展乡村产业等方式,实现农村有序发展。
其一,精准识别不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基础,确定区域人口的基本需求与发展要求。将人口结构作为村庄分类的关键识别要素,利用多样化的方法手段测算不同区域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对不同区域农村常住人口基本需求供需情况的精准认知,并以此为依据确定该地区的未来发展重点与方向。
其二,发挥县乡国土空间规划的空间统筹和要素保障作用,顺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整合优化现有资源,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以经村级议事协商、自愿推进为前提,适时引导、有序推进撤村并居。合理规划村落承包地与宅基地等空间布局,以实现村民基本生产资源保留与空心化村落集聚提升的双重效用,促进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推进。
其三,根据区域常住人口需要,有针对性地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适时推进乡村适老化改造;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推动乡村治理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衔接,注重多元主体的嵌入式参与,挖掘内生治理资源和力量,实现有效治理;合理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不断推进与自身人口结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乡村振兴实践,实现村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创通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